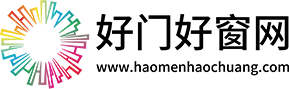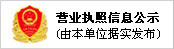8個月前,ofo澳洲前策略執(zhí)行長Scott Walker在抨擊競爭對手oBike和Reddy“像牛奶工一樣”亂扔共享單車時,或許并未想到自己所在的公司也會殊途同歸。
“這些運營商沒做好充足準備就沖進市場,把秩序搞得一團糟,讓我們的工作更加困難。”Scott Walker當時向澳洲媒體抱怨道。
2017年10月24日,經過半個月在阿德萊德試運營后,ofo宣布正式入駐澳大利亞悉尼。
2018年7月10日,ofo向澳洲各大媒體宣布:根據公司“戰(zhàn)略性決定”,將在未來60天內逐步結束在澳大利亞的運營,最終撤出澳洲市場。至于是否有更具體的原因,ofo也一直未對界面新聞做出回應。
“在這過程中,ofo共享單車將被逐漸移除并放置到倉庫中。”ofo一位發(fā)言人表示,這對ofo并不是一個輕松的決定,ofo澳洲將負責任地進行善后工作,并“以國際視野聚焦優(yōu)先市場”。
Scott Walker并未見證ofo在澳洲的尾聲一幕。今年3月,他離職了。
 ofo共享單車,界面記者攝于悉尼街頭
ofo共享單車,界面記者攝于悉尼街頭水土不服
“這(ofo撤出澳洲)是遲早的事。”澳洲ofo用戶、互聯網公司Ansarada產品經理Rebecca Cooper在推特評論道。
“我用過好幾次ofo共享單車,感覺特別好用;但漸漸地發(fā)現越來越難找到車,因為最終發(fā)現它們的地方不是在水溝里,就是像這樣堆成山。”
 推特截圖
推特截圖共享單車登陸澳洲會遭遇很多挑戰(zhàn),但這個難題或許是最出乎運營商們意料之外的:用戶教育,或者不客氣地說,用戶素質問題。
與中國共享單車被據為私有的問題不同:在悉尼和墨爾本,大量共享單車被惡意破壞,它們不但沒有被妥善上鎖及擺放,而是被扔進河里、火車軌道邊,堆在街角,甚至掛在樹上。
共享單車也因此遭到當地居民強烈反對,認為它們是“移動障礙物”,是“絆倒行人的隱患”。
在ReddyGo、oBike、Airbike等共享單車進入悉尼短短3個月內,悉尼市政廳就收到了29個對共享單車的投訴。oBike進入墨爾本后,更因為收到的投訴太多,而被維州環(huán)保局(EPA)勒令整頓,否則將開出每單高達 $3171.4的罰單。
有了前車之鑒,ofo在進入澳洲市場時信誓旦旦保證,將比其他運營商“更負責任”。
的確,ofo提出了很多解決方案。其中包括根據悉尼六個區(qū)議會出臺的《指導原則》,引入“地理圍欄(geo-fencing)”技術來劃分停車區(qū)域,同時配備經驗豐富的本地化運維團隊,確保單車有序停放并及時維修。當然,在人力成本高企的澳洲,這也增加了ofo的運營成本。
“我們在每個市政廳的范圍內提供25到30個推薦停放區(qū),并在一些停放區(qū)附近有監(jiān)控錄像,以監(jiān)視那些破壞者。”Scott Walker當時向公眾介紹道,用戶通過ofo的“電子圍欄”GPS衛(wèi)星定位技術,可以通過“建議停車區(qū)域”找到最合理的停車區(qū)域。
 ofo推薦停放區(qū),ofo官推配圖
ofo推薦停放區(qū),ofo官推配圖一旦用戶試圖把車停在指定區(qū)域之外,用戶的信用積分就會被扣除;在扣除一定分數之后,用戶就會被拉入黑名單。
“這就是我們區(qū)別于競爭對手的做法:從第一天運營開始,就積極主動地尋求最佳運營方法。”Scott Walker說。
然而,“最佳運營方法”只稍微推遲了ofo退出澳洲市場的時間。
在新加坡共享單車公司oBike、本土公司Reddy Go 上個月相繼宣布從澳洲市場撤出之后,ofo也難逃相同命運。
 被亂放的摩拜和ofo共享單車,界面記者攝于悉尼街頭
被亂放的摩拜和ofo共享單車,界面記者攝于悉尼街頭供大于求
如果說管理用戶很棘手,更深層次的問題或許在于供大于求的供需不平衡問題。
共享單車運營商們在進入市場時都相信,在澳大利亞共享單車的出現能夠很好的彌補交通出行的空白,同時短途點到點出行解決方案也有著很大的市場。
然而從用戶的角度來看,感受卻非常不同。
“(ofo退出澳洲)不意外啊,因為用的人確實不多。”在澳華人Mandy告訴界面記者,平時幾乎看不到本地人在用共享單車,她認為主要原因是在澳洲生活通勤不是很需要共享單車。
“在國內,騎小黃車通常是接駁地鐵與公司之間的距離,就是一公里左右、步行有點遠打車又沒必要那種情況。但在澳洲工作地點通常就市中心那幾個區(qū),坐火車地鐵都可以直達,墨爾本CBD還有免費電車;而如果在郊區(qū)工作,那肯定都開車了。”
 悉尼唐人街附近很多共享單車但騎的人不多,界面記者攝于悉尼街頭
悉尼唐人街附近很多共享單車但騎的人不多,界面記者攝于悉尼街頭Mandy表示自己用過幾次共享單車,體驗都一般,“澳洲地勢不平,起伏很大,很多時候不適合騎自行車”。
悉尼華人留學生小J也有類似的感受,他告訴界面記者:“用共享單車的人不多,因為感覺不是很方便——車很少,還要戴安全帽。澳洲不像中國街區(qū)這么密集,交通主要靠汽車火車,自行車的用處太小了。”
 在澳洲騎共享單車要戴頭盔,界面記者攝于悉尼街頭
在澳洲騎共享單車要戴頭盔,界面記者攝于悉尼街頭事實上,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今年5月的一項研究就發(fā)現,澳大利亞是世界上共享單車使用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在悉尼,共享單車平均每天被使用0.3次,而在其他國家,這個數字通常為2~6次不等。
行業(yè)及市場研究機構IBISworld資深分析師Kim Do曾向澳洲新聞網站News.com.au談論過這個問題,她認為ofo等共享單車在澳洲市場陷入泥濘的最主要問題,就是供大于求。
“去年多家共享單車新創(chuàng)公司涌入市場、爭奪用戶,然而共享單車用戶卻沒有隨著單車數量的增加而增長,導致出現現在的局面。”Kim說道。
此外,人口基數較小也是造成供大于求的原因。據澳大利亞統(tǒng)計局(ABS)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16年12月全澳人口數接近2500萬,比國內一線大城市人口多不了多少。
而且在人口的分布層面澳洲與中國不同,居民大部分分散在市中心以外的郊區(qū)。譬如,墨爾本CBD只有36平方公里,覆蓋的人口數量只有約14萬人左右。
今年3月,ofo官方linkedin賬號發(fā)布了一條推送,慶祝ofo進入悉尼市場以來達成32萬總使用次數。
然而據QuestMobile數據統(tǒng)計,ofo全球用戶2018年5月總使用次數高達9.62億次。
政府的阻力
壓倒共享單車在澳發(fā)展之路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許是澳洲各地政府的態(tài)度。
相比中國、新加坡等政府,澳洲地方政府對共享單車始終抱著可有可無、有所保留的態(tài)度。
以oBike為例,當oBike的共享單車遭遇嚴重破壞時,墨爾本政府并沒有給予oBike太多耐心和支持。墨爾本市長甚至表示,如果oBike不能管理好共享單車,就會被取締。
政府這樣的態(tài)度,歸根結底是因為共享單車的發(fā)展模式與澳洲城市的發(fā)展規(guī)劃并不完全吻合。
如Mandy和小J所說,按照傳統(tǒng)的出行習慣,澳洲本地人大多數時候用不著共享單車,但被廢棄的共享單車卻給生活環(huán)境帶來了負面影響,給政府增加了治理成本和負擔。
 澳洲媒體The Age報道配圖,攝影師:Joe Armao
澳洲媒體The Age報道配圖,攝影師:Joe Armao相比之下,ofo已經算是“含著金鑰匙出生”。據Scott Walker此前表示,ofo是首家獲得澳大利亞政府運營許可的共享單車平臺,此后又獲得了自行車權威機構——新南威爾士州(下稱“新州”)自行車協(xié)會(bicycle NSW)的背書,因此也獲得了更多與地方議會、政府和自行車利益相關方進行合作的空間。
事實上,今年3月11日,ofo還與新州自行車協(xié)會聯合舉辦了澳洲最大女性社群騎行活動“Gear Up Girl”。

不過,在談到共享單車亂停放問題時,新州交通部長Andrew Constance卻直言不諱:“這些亂扔亂放的自行車就像到處被廢棄的超市購物車一樣惡心,它們必須被清理掉。”
就共享單車紛紛退出市場,新州州長Gladys Berejiklian也接受了澳洲媒體2GB的采訪。
“有(共享單車)公司說政府制定的規(guī)則桎梏了創(chuàng)新,那是他們自以為是。也有可能是人們根本不想用他們的服務,或根本不喜歡他們的運作模式。”Gladys Berejiklian說道,“如果他們決定不再提供服務,無所謂——我認為我們有足夠好的交通網絡和選擇,即使沒有共享單車也沒關系。”
Gladys Berejiklian還強調,共享單車是私人企業(yè)提供的服務,而非政府提供的服務:“我們會盡可能為企業(yè)提供創(chuàng)新的機會,如果有新的出行方式、有更輕松的方式,我們會讓這種選擇有實現的機會。”
然而,如今這種選擇實現的前景已經驟然黯淡。
ofo繼撤出中東及以色列市場再撤出澳洲市場,未來在國際市場的表現仍待觀察。
與此同時,ofo在中國市場最大的競爭對手摩拜仍在澳洲市場堅持。

2018年7月11日,摩拜澳洲宣布推出了電動單車產品“E-Bike”,并發(fā)了一則推特的推送,問用戶:“如果E-Bike能在爬坡的時候助你一臂之力,你會更經常用Mobike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