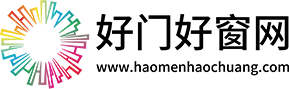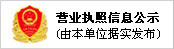1月4日傍晚,趙偉走出深圳市民中心,結束了一天工作,他代表自己的公司剛參加完一個由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主辦的P2P網貸合規整改研討會,當天會議上深圳市金融辦、深圳銀監局相關負責人聽取了深圳十幾個平臺的整改進展。
很多年以后趙偉依然會記得這個跨年的冬天,他感覺自己要重新找工作了。事實上,對于包括他在內的很多互金人士,都深切地感受到去年ji壓。
一石掀起千層浪的是:2017年12月中旬網貸整治辦下發的一紙文書,簡稱57號文,原文件全名“關于做好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整改驗收工作的通知”,具體為要求各地最遲應當于2018年6月末之前完成整改驗收以及后續備案登記工作;對于在2016年8月24日后新設立的網貸機構或新從事網絡借貸業務的網貸機構,原則上不予備案登記。
通往備案的路途上可能布滿“荊棘”,留給他們的時間也不多。“大額標的存量資產的清算、資產轉型、信息披露”等或會給平臺帶來優質資產獲取的困難、成本的增加,貸款余額的控制,這些都需要他們逐一去解決。現在,對于他們而言,最大難題莫過于大標(大額標的)處理,像催促借款人提前還款、摸索違規資產剝離處置等已提上議程。而那些“8.24”后成立的新平臺或許更不知所措,對于新平臺的界定依然模糊,其或會打著合規概念擦邊球,聲稱自己是在8.24之前上線開展業務的。
就在這樣一個冬天,有人沉著應變、有人掙扎求存……等待他們的是什么?5個月后謎底揭曉。
大標清算加快
去年6月份,深圳開始進駐平臺檢查。“這周的數據是怎么樣的,整改的進度如何?”趙偉回憶,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每周都要去深圳金融辦報數據。去年3月,北京監管部門向各網貸平臺下發了一份名為“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事實認定及整改要求”(下稱《整改要求》)的文件,共計148條。《整改要求》發布后,全國各地都在陸續跟進,深圳的檢查也是依照這個“148條”進行的。
廣州乃至廣東的監管也在行動。從2016年年底開始,廣東省金融辦、省銀監局創新處、省工商局、省公安局的相關部門成立了一個聯合檢查小組對直屬四家企業進行檢查。
檢查主要從這幾個方面進行。首先是現金流,廣東銀監局開發了一個模型,能快速檢測出平臺是否存在虛假標的、違約、自融等問題,除此之外還有資產、利率、投資者情況、系統情況,是否有銀行存管,公司治理、從業人員等等。“全部都要查,部分問題比較多的平臺駐場了幾個月。檢查完后監管會給到平臺一個反饋意見,后面需要平臺每個月都提供一個合規的進展匯報。”一位在上述四家直屬企業其中一個平臺工作的副總對本報表示。
對于平臺而言,整改最大的難題是對大額標的存量資產的處理。趙偉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原來按照監管的要求只要新標停發,舊的大標按照正常的到期流轉完成即可,后來監管要求必須提前做好清算。“當時我們也跟相關的部門溝通一下子發小標的話,由于資產不同不可能馬上能找到很小的標頂上,所以溝通得出的結論就是把標的的額度都縮小,目前最大的標的在600萬左右,更大的標的都自然流轉完成,還沒有流轉完成的就是這種百萬級別的標。”趙偉說。
2016年8月24日發布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簡稱“《暫行辦法》”)幾乎宣判了大標的“死刑”。標的涉及金額比較大,對于平臺來說有一定的壓力,深圳某P2P平臺的首席運營官對經濟觀察報表示,他們的做法是讓大標借款人提前還款,他們從前年8月24日之后已經沒有發特別大的標的,并且陸續跟大標的借款人溝通要求提前還款,計劃今年3月底前把所有的大標都清算完成。
《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同一借款人在同一網貸機構及不同網貸機構的借款余額上限。同一自然人在同一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平臺的借款余額上限不超過人民幣20萬元;同一法人或其他組織在同一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平臺的借款余額上限不超過人民幣100萬元;同一自然人在不同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平臺借款總余額不超過人民幣100萬元;同一法人或其他組織在不同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平臺借款總余額不超過人民幣500萬元。
上述廣東金融辦直屬檢查平臺的副總也存在同樣的困惑。“我們平臺上有一些大標的是兩三年期,可能到今年四月份還沒辦法結束,我們有一個平行的公司,想做一個資產剝離,因為條例里面有提到可以處置和剝離,這個需要跟監管進一步溝通,目前還沒有定論。”上述副總說。
信批的“苦惱”
“什么時候會有新的產品,為什么現在可投資的產品比較少?”有投資人找到上述副總的平臺咨詢。
“存量的資產在壓縮,貸款業務要控制,一定是減少不可以增加,去年一月份監管來查的時候是多少的貸款余額,理論上是說不能超過這個額度。”上述廣東金融辦直屬檢查平臺的副總回應投資人。
《2017中國P2P網貸年度簡報》顯示,截至2017年年末,P2P網貸貸款余額為12,160億元,待還利息約1119億元,約為本金的9.2%。貸款余額較去年同期增長95.1%,較11月末下降0.9%,已連續三個月呈下降趨勢。上述副總對經濟觀察報記者感慨,目前對網貸整個監管體系一定程度來說比銀行還要嚴格,因為它很透明。
2017年8月24日,銀監會發布《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信息披露指引》,2個月后,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正式向會員單位下發《互聯網金融信息披露個體網絡借貸》團體標準,結合銀監會的信批指引進行了適當的完善。據零壹數據統計,截至12月末,接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互聯網金融登記披露服務平臺"的網貸機構已達116家,據116家互聯網金融平臺披露的最新數據,這些平臺累計交易額達到3.33萬億人民幣,交易總筆數達到19077萬;不考慮借款人跨平臺融資以及投資人在多個平臺投資等情況,人均借款額和人均投資額分別為4.6萬元和9.0萬元。
上述副總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按照信批的要求,他所在的平臺在信批上還是有難度的。例如要求平臺擁有客戶在央行征信報告,但是P2P的公司沒有資格接入央行的征信系統,只能讓客戶打印一份給平臺,如果客戶以前都是純線上作業的話就沒有相關記錄了;再如每個月披露平臺的財務報告,財務人員每個月都要忙于出報表,成本比較高。廣東省金融辦目前還沒有對披露頻次、內容有具體的要求,以后應該會有一個統一的約束。
根據銀監會和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信批要求,趙華所在的平臺可能還不能完全達到要求,但按照他的理解,從備案的角度來說監管并沒有明確說信批要具體做到哪一步,更多的信批對于他們獲取資產是有難度的,特別是目前他們優質資產比較緊張的情況下,希望能適當保護資源。“我們盡量在做修改,之前也專門針對信息披露做了一版改版,推出了一個信息披露的欄目,披露公司的股權結構、背景、高管信息,包括一些風險提示的調整例如投資人注冊時候要手動填寫一些信息而不是默認勾選。”
打概念“擦邊球”
還有一群人也很郁悶。這群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2016年8月24日后新設立的網貸機構或新從事網絡借貸業務的網貸機構工作,有些剛見證平臺完成一輪融資,有的剛跳槽到這種新平臺不久。
從“57號文”看,“新平臺”直指兩類:一是指“824”后新設立的網貸機構,即公司的設立時間在2016年8月24日之后;二是公司設立時間早于2016年8月24日,但網貸業務上線時間在此之后。按要求,在本次網貸風險專項整治期間,即2018年6月底之前,這兩類平臺原則上不予備案登記。
據網貸研究中心統計,截至2017年11月底,“824”之后累計新上線平臺數量至少有162家,月均上線平臺數量不足10家,直接導致正常運營平臺數量大幅度下降,從2015年12月最高的3500家已經下降至目前不足2000家。162家新上線平臺中,目前仍在正常運營的平臺數量為95家,停業及問題平臺數量為67家。
就目前而言對于這些新平臺最大的爭議是如何界定新開展業務,究竟以第一個標的發放時間還是第一個用戶完成注冊-實名-綁卡-投資整個過程為準,57號文都沒有給出明確的指引。據經濟觀察報了解,一家2016年8月24號之后才上線的平臺就打起概念的“擦邊球”。它在2015年的時候使用舊版系統開展過一些業務,在2016年8月24號后重新上線了新的系統,原來的業務標的記錄都沒有了,而這家平臺現在就聲稱自己就是2015年開始開展業務的,不屬于57號文的新平臺范疇。值得一提的是,這家平臺在今年11月拿到了A輪融資。“由于57號文沒有具體說明,而且各地執行情況不一,不確定上述平臺所說的舊版系統是否在考慮范圍之內。”趙華對經濟觀察報表示。不過他認為新平臺還是存在很大被淘汰的風險,尤其是這種剛剛獲得融資的企業,投資人的錢很可能會打水漂。
留給新平臺的選擇的確沒有多少。“之前有人說可以通過收購一些合法合規的平臺來完成整改驗收,但是現在很多在8月24號之前就已經開展業務的平臺都生死未卜,收購的錢還是可能打水漂。”趙華說。
網貸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從目前退出新平臺的現狀看,截至2017年11月底,新平臺退出的數量有67家,退出類型分別為停業、提現困難、跑路和轉型,數量分別達到了27家、22家、16家和2家,新平臺更多的以惡性退出為主,可以看出新上線平臺的投資風險更大,這些平臺能等來屬于它們的春天嗎?這個冬天怎么過?